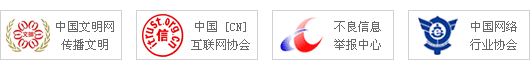據《勞動報》報道,昨日起,上海正式調整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從1450元調整到1620元,增加170元,增幅達到11.7%。然而,本報記者走訪發現,新政實施后,多數企業僅被動調整了最低工資,而出于降低成本考慮,原先在“臨界線”之上的職位薪資水平基本沒變化,這也造成不少員工抱怨自己遭遇“變相降薪”。
基層崗位未出現萎縮
昨日,在閔行一個職介所內,經過全新調整后的招聘崗位已經出臺。“在上周末,我們已經通知企業,周一起的招聘待遇必須進行調整。”閔行區外勞所相關負責人陸小燕如此表示。
此前有業內人士指出,最低工資標準大幅上調,會使企業勞動力成本短期內大幅提高,加大經營壓力,因此可能造成崗位縮水現象出現。但據記者在閔行、黃浦、寶山的調查發現,現實情況并非如此,至少在當前發布的基層一線崗位中,企業并沒有減少招聘職位。
一家勞動力中介服務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事實上,這些拿著最低薪資的崗位始終處于缺人狀態,“不是過溢,而是壓根招不滿。”
“從過去統計來看,開出最低薪資的企業數量也并不多。”黃浦區職介所負責人胡潔靜表示,這些多聚焦在一些保潔、物業、流水線操作工等對技術要求簡單的領域,而其中不乏一些公益性崗位。由于多為“臟累差”,因此才會缺口較大。
收入差距越來越小
值得關注的是,最低工資上調后,一部分企業員工的抱怨聲開始出現。記者了解到,這些勞動者原先的薪資多只有2000元左右,甚至不少月薪僅為1700至1800元。在未調整之前,他們的月薪與最低工資差距達到300元以上,如今相差無幾,幾乎逼近最低工資臨界線。對此,這些員工甚至認為自己是“降薪”。
讓這些員工期盼的是,企業在上漲最低工資的同時,是否也能“跟風”調整這批“夾心層”的薪資?可惜的是,這個愿望多數要落空。
“最近3年,我們廠的平均工資翻了兩倍多。”一家針織廠負責人告訴記者,尤其是“招工荒”更是讓外來務工人員的薪資期望值普遍大幅提高。他坦稱道,面對最低工資調整,企業只能被動執行,但是如果要進行“普漲”,成本實在太高。
胡潔靜也表示,一線基層崗位的底薪一般跟著最低工資走,最近幾年最低工資陸續上調,漲薪情況相對較明顯。但一些原先中等收入的群體,其工資待遇由于“原地踏步走”,反而因最低工資調整帶來的受惠不大,“根據以往經驗來看,部分企業也會小幅調整,但延時往往要達到半年。”
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最低工資針對的是社會底層的困難群體,每一次上漲都有其積極意義。”交大教授、勞動經濟學專家陸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帶來了“夾心層”的困惑。
陸銘指出,導致這些群體不滿的真正因素,其實并非是“普漲”,而是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收入跑不贏CPI。對此,陸銘認為,除了最低工資標準應當穩步上調以外,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也亟須建立,“重要的是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加快建立民主參與企業工資分配決策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