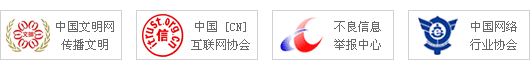對于許多人,尤其是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翻譯軟件的新突破提供了另一個借口,他們不必為學習一門新語言所需的所有時間、精力和社交尷尬而煩惱。他們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論點。大多數人不會經常出國旅行。即使您這樣做了,您通常也可以在主要旅游目的地使用英語(或者,在較小程度上,另一種主要的世界語言)。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是如此;在我們的數字時代,整個互聯網都可以使用您喜歡的任何語言。
我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不是君士坦丁堡)寫信(現在他們希望你稱它為 Türkiye)。作為一個說珍貴的小土耳其語的人,我的某些部分希望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后語言障礙的世界中。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不這樣做。
從最平庸的層面開始,一個人在本國以外的移動覆蓋往往參差不齊或價格昂貴。我的美國朋友有時會取笑我浪費時間學習其他語言而不是像購買 NFT 這樣實用的東西,但是當我們在切什梅郊外的某個干旱山谷徒步旅行時迷路時,每個人都很高興我在這里度過了這次飛行的速成課程用土耳其語。僅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從秘魯到奧地利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真正的生活不會發生在 Web 3.0 上。
學習另一種語言仍然有令人信服的實際、智力、文化和專業理由。首先,雖然翻譯技術在過去十年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即使是在歐洲主要語言中,它們仍然難以實現完整的句子;對于更具異國情調的人來說,它們提供的喜劇多于實用價值。忠實地翻譯口語是很棘手的,像谷歌和多鄰國這樣的行業領導者往往更喜歡在切諾基或多斯拉克語中添加基本產品的簡單業務,而不是加強意大利語和土耳其語,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可能仍然是一個問題。
即使你從不旅行,學習一門語言也能豐富你的生活。如果你對文學感興趣,讀一個翻譯當然比什么都不讀好,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文化視角的扭曲。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怪誕有趣的地下手記的標準英文版開頭是:“我是個病人。我是一個懷有惡意的人……” 英文翻譯為“spiteful”可能會為嚴謹的維多利亞人帶來一記重拳,但原始的俄語zloi意味著更類似于“邪惡”的意思。
《堂吉訶德》中多次提到背信棄義的裁縫(sastres),這在英語中似乎很奇怪,但如果人們熟悉sastreria在現代早期西班牙語中的狡猾含義,這就是笑話的一部分。我在原版中翻閱弗朗茨·卡夫卡的《審判》時玩得很開心,因為卡夫卡利用德語不可思議的靈活性來構建瘋狂的連續句子,強化了荒謬的敘述。
一個人甚至不能完全依賴用自己的語言編寫的文本,如果沒有一些背景知識來了解它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詹姆士國王圣經中的一項禁令認為,“尊重他人是不好的。” 這節經文的真正目的是阻止不公正的偏見,當時講英語的人會這樣理解。但是人們希望今天的基督徒不要太從字面上理解被普遍認為是最權威的《好書》的版本。
當同名的詹姆斯國王的孫子詹姆斯二世看到新建的圣保羅大教堂時,他將其描述為“有趣、可怕和人工”。他的意思是它令人賞心悅目,令人敬畏,并且是工藝的勝利。下次你閱讀任何最初用完全不同的語言寫成的書時,請記住微妙的語義變化對意義的影響有多大。
說另一種語言也可以提升你的職業生涯,即使你不是很擅長它。我是拉丁文的新手,我當然從沒想過會用它來做演講。但人們經常評論它被列在我的簡歷上,而且它確實出現在所有地方,即使在金融等人們喜歡認為自己超現代和實用的領域也是如此。說另一種語言有點像擁有物理學背景:即使你從未將它應用到你的工作中,人們只是認為你更聰明。
當然,如果你能將你的語言技能應用到實際的交流中,那是最好的。畢竟,語言是關于與人聯系的。下次你出國或與其他國家的人會面時,試著學習兩三個基本短語。我保證它會讓任何互動變得更溫暖、更有意義。
不管技術有多好,沒有人愿意通過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機器人進行交流。學習一門語言在精神上、社交上和精神上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挑戰。在我們日益數字化的世界中,這不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