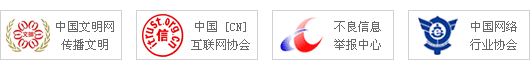不久前,美國作家戴夢(Michelle Dammon Layalka)在聯(lián)合國中文教學(xué)部和中文書會聯(lián)合舉辦的講座上介紹了她的英文新書,《吃苦》。
作家本人在中國生活了13年,能講一口流利中文,目前全家仍住在北京。她介紹說,這本書詳細(xì)敘述了她在西安工作和生活期間所認(rèn)識的八個農(nóng)民工的人生經(jīng)歷,并以此來向美國人(或者說,能夠閱讀英文的人)介紹在中國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和社會巨變背后兩億多特殊人群,農(nóng)民工,的生活。
首先讓我好奇的是英文書名,Easting Bitterness,這顯然不是標(biāo)準(zhǔn)的英文詞匯,而是完全從中文“吃苦”兩個字直譯過去的。她解釋說,她找不到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英文詞匯能夠?qū)⒅形?ldquo;吃苦”兩個字的內(nèi)涵恰如其分地表達(dá)出來。我在美國學(xué)習(xí)和工作20多年了,英文水平還湊合,腦子里閃過幾個相近的單詞,如enduring, suffering, bearing hardship, grit, 但似乎都不能充分表達(dá)“吃苦”的全意。只有感嘆,看來,世界上只有中國人懂得“吃苦”,外國人不知道吃苦。
書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的農(nóng)民工:擺菜攤的,走街串巷的磨刀師傅,美容業(yè)的低級模特,回收廢品的工人,保姆,等等。他們原來都生活在農(nóng)村,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他們離開了故土和家人來到城市尋找工作機(jī)會,其中,那位保姆離開自己的孩子,到城里給人家?guī)Ш⒆印K麄兊哪康亩际菫榱烁纳谱约阂约凹胰说纳睢W髡咧胤从沉诉@些農(nóng)民工吃苦耐勞的品質(zhì)和對生活積極勤奮的精神;同時也反映了,由于中國巨大城鄉(xiāng)差別和不合理的戶口等社會制度,這些農(nóng)民工在設(shè)法融入城市過程中的艱辛。當(dāng)然,書中也描述了一位農(nóng)民拿到土地征用費后變成了無所事事一天到晚打麻將的混混兒。
這些故事本身對我這樣曾經(jīng)在中國插過隊又一直關(guān)注著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人來講,并沒有什么稀奇感。但對于許多外國人,特別是那些沒有去過中國,或者只是走馬觀花地看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這本書可以幫助他們更多地了解中國。
從講座上一些外國朋友(大多是在聯(lián)合國中文教學(xué)部學(xué)習(xí)中文,對中國友好而好奇的聯(lián)合國國際職員)的提問還是可以看到,要想讓外國人真正了解中國在過去30年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巨變是不容易的。大多數(shù)的提問主要集中在這些農(nóng)民工由于戶口制度而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福利,子女教育,醫(yī)療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例如,詢問有沒有非政府組織幫助他們,政府對他們提供什么福利。這些問題沒有錯,特別是從聯(lián)合國一些以推動人權(quán),平等,共同發(fā)展為己任的國際職員嘴里提出來非常自然(我事后看到的一些美國人寫的書評,也基本上集中在這些問題上)。但是,我感到他們并沒有能夠真正理解這些故事,沒有真正理解“吃苦”的涵義。
我在講座上與作者交換了我的感想,事后又補(bǔ)充了一些想法。
首先,我們應(yīng)該感謝作者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向外國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的獨特視角。讓他們知道,中國在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僅次于美國的中國GDP總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樓大廈,都是由類似這本書中的主人公那樣的幾億農(nóng)民工和其他一些勞動者吃苦耐勞,辛勤努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
作者在她的開場白中說,由于中國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5億多人被從貧困中解救出來(她用的是英文的被動語態(tài))。我告訴她,我平時用英文向各國朋友介紹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時也是這樣說的,但是,在今天聽了她介紹了《吃苦》這本書之后,我覺得,以后我們不應(yīng)該再用被動語態(tài),而是要用主動語態(tài):5億多人經(jīng)過他們辛勤勞動擺脫了貧困。誠然,是改革開放政策從制度上調(diào)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各種各樣的短期計劃和長期規(guī)劃,以及謹(jǐn)慎的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固然也很重要,但是,中國老百姓的勤勞和智慧是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是奇跡,不是魔術(shù)般變幻出來的,更不是上天的恩賜。
從一些聯(lián)合國國際職員的提問,使我聯(lián)想到中國的發(fā)展經(jīng)驗與國際社會為促進(jìn)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推行的一些發(fā)展理念之間的關(guān)系。
在過去20年里,全世界擺脫貧困的人口中,70%來自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在擺脫貧困方面取得的成就,聯(lián)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中的首要目標(biāo),在2015年將全球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基數(shù)上減少一半,將無法實現(xiàn)。
但是,國際社會并沒有認(rèn)真而虛心地去研究中國的發(fā)展經(jīng)驗,往往強(qiáng)調(diào)中國發(fā)展的特殊性,認(rèn)為不可能在其他國家復(fù)制。
相反,在國際社會推崇的發(fā)展理念和政策中,過分強(qiáng)調(diào)發(fā)達(dá)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官方援助作用。事實上,中國和東南亞的發(fā)展,幾億人脫貧,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不是依靠發(fā)達(dá)國家的官方援助。
此外,國際社會還過分強(qiáng)調(diào)以政府推行“福利社會”政策來解決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困和其它一些發(fā)展問題。一些國際社會的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往往混淆發(fā)達(dá)國家存在的貧困問題和發(fā)展中國家存在的貧困問題。在發(fā)達(dá)國家人均收入4-5萬美元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政府的再分配和“福利社會”政策來解決一部分人的貧困問題(當(dāng)然,過高的福利社會也會給發(fā)達(dá)國家?guī)韲?yán)重問題,例如,希臘目前的債務(wù)危機(jī))。但是,在發(fā)展中國家,例如一些非洲國家,60-7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不可能靠政府的再分配來解決大多數(shù)人的貧困,只有靠合理的機(jī)制將老百姓的經(jīng)濟(jì)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通過經(jīng)濟(jì)增長來解決貧困問題。中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正是這樣做的。
當(dāng)然,在經(jīng)濟(jì)總量增長到一定水平之后,政府應(yīng)該逐步健全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加大政策力度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籌的醫(yī)療、工傷、失業(yè)等社會救助和保障體制,逐步縮小農(nóng)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在這些方面的差別。中國還應(yīng)該盡快取消戶籍制度。
但是,“吃苦”恐怕仍然還是大多數(shù)中國老百姓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必須繼續(xù)保持的精神。“吃苦”也是任何發(fā)展中國家要想真正擺脫貧困的必由之路。